“教科书影响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专访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石鸥
Editor:admin Source:best365体育官网登录入口 Date:2016-10-19
人物简介:石鸥,湖南新宁人,1982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学院(best365体育官网登录入口前身)。现任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特聘教授、课程与教学论博士点负责人、课程教学研究所所长,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基础教育教科书研究与评价中心主任,全国教育文物研究会理事长,全国教育实验研究会副理事长,全国教学论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教育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级教学名师。出版学术著作、教材40余本,在境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100多篇,数十篇论文被全文或部分转载或被评论。主持各级课题近40项。近年来,依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收藏的大量教科书实物,石鸥和其团队先后推出《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中国近现代教科书史》《新中国中小学教科书图文史》等系列大型教科书研究成果,先后获北京市哲社成果一等奖、教育部人文社科成果二等奖等多项奖项,正在筹备全国第一家教科书博物馆,在海内外引起了较大的学术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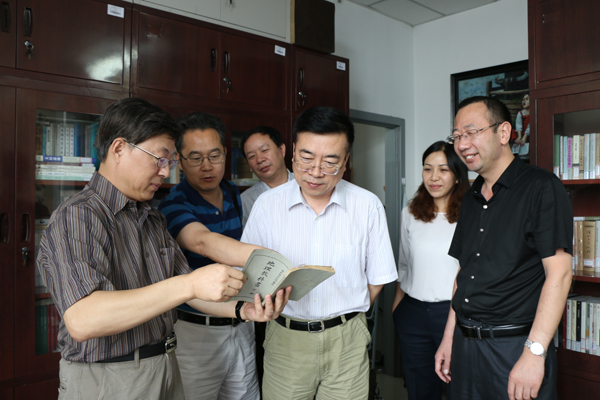
石鸥教授正在向中国教育研究院院长、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中心主任田慧生研究员介绍教科书博物馆的收藏
在首都师范大学东校区B区7楼,有一个不起眼的房间,这里是首都师范大学教科书博物馆。在这儿,近2万册老课本静静地躺在书柜里,无声地诉说着百年间的变迁。博物馆里的老课本,上迄清末,下至当代,横跨百余年,品种齐全,类型多样,所有这一切都是石鸥殷勤收集的结果。从20世纪90年代收藏第一册老课本开始,他的脚步一直没有停下。尽管这个领域起初似乎有点儿“冷”,但他硬是凭着20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使老课本进入公众的视野,使教科书研究成为教育学研究领域的一门“显学”。圈子里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说有一个湖南的石鸥教授专门收藏老课本,搞得书商们纷纷抬价,把教科书市场都给炒贵了,炒高了,其实此时石鸥已经举家迁往北京。面对越来越贵的老课本,面对经费的拮据,很多时候,他还是自掏腰包忍痛买下,就为了给这些发黄发脆的老课本找一个“家”。凤凰卫视在采访时总结说,“收藏老课本是石鸥教授最值得骄傲的财富,他用那一本本泛黄发旧的书留住了绵延上百年文化的根。”

北京市委组织部长姜志刚参观石鸥教授的教科书博物馆
从1978年进入湖南师范学院教育系学习开始,石鸥与教育的缘分就未曾中断,他痴迷于教育与教学的初心也未曾改变。不管是早期开创和引领国内“教学病理学”研究、探索“教学别论”,还是逐步转向对百年中国教科书的研究,他总能占领一个个教育研究的高地,并将自己对教育的执着与热情,化为推动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的不懈动力。2013年11月,石鸥在首都师范大学倡议并运作了“第一届海峡两岸教科书研究高峰论坛”,翌年,大陆地区第一本研究教科书的专门刊物《教科书评论》出版发行。从此,举办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的教科书研究高峰论坛和出版刊物成为每年教科书研究界的盛举。每一次论坛,我们都能看见石鸥穿梭于各个会场的身影,都能聆听到他那略带湘韵的声音,他毫无保留地将廿年间致力于教科书的收藏、整理、研究的体会和盘托出,以抛砖引玉,以奖掖后进。海峡对岸的几位教科书研究领域的健者,他们联袂拟定“石破天惊小课本,鸥心沥血大启蒙”的赠言,并专门邀书法家书丹。如今,这幅匠心独运的“藏头”对联就挂在石鸥办公桌对面的墙上,每一位到访石鸥办公室的人,都会在此驻足,吟诵再三。这幅小小的对联,既是石鸥的为学之道、为人之道的缩影,也高度概括了教科书的价值。
师大之情
无论是负笈求学的四年,还是为师任教的卅余年,每每忆起,石鸥都对湖南师大充满了浓浓的思念与眷恋。1978年,仍在工厂做工的石鸥突然听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他来不及系统地复习,就匆匆走进了考场。在离开学校的日子里,他做过知青、当过工人,而书籍一刻也不曾离开他的床头。他成功考入湖南师范学院,成为了“文革”后湖南师范学院教育系第一届本科生。
石鸥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读本科时和同学们共同学习的场景。同学们尽管年龄大小不一,但都特别珍惜学习的机会,无一例外。“当时大家求知欲望特别强,感觉知识世界的大门突然敞开了。‘文革’期间,大家在农村、在工厂,基本上把能找到的书都看完了。当时考上大学的都是在农村没有把书丢掉的人,这些人,一恢复高考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就来考了。”那时候,即使是星期天,大家也不会睡懒觉,都觉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所有同学都很早起床跑步,早晚主动读英语,茶余饭后讨论的都是学术问题。“那时候的书很少,当时溁湾镇有一家新华书店,里面和专业相关的书都被他们买完了。没有书可买,就借书;借到一本书不容易,就夜以继日地读。宿舍晚上11点熄灯,而求知的渴望熄灭不了,大家就到洗手间借光看书,这两小时是你,那两小时是他,洗手间的长明灯照亮了知识的星光大道,指引他们前行的方向。当时书籍更新频率很低,为了及时获悉国际上的学术热点,他们往往通过《读书》杂志来了解国内外的情况。
由于“文革”的影响,教育系老师被压抑了很多年,长期远离教育领域研究。“文革”结束后,他们重新焕发青春,全副身心都投入到教学和研究中。因为他们以前也没有带过学生,所以就在摸索中探索指导学生的方法,教学相长,师生关系非常融洽。本科毕业论文写作期间,石鸥曾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给当时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知名学者写信求教,不久就收到回信,这种记忆长存在他的内心深处,也使他日后即便遇到素昧平生的学生,也毫无保留地予以指导。在他的记忆中,当时的老师们学术功底扎实,又关心学生成长,师生经常沟通交流。
教育系招收的第一届本科生有45个,毕业后大多数都直接走上工作岗位。石鸥也不例外,本科毕业后,他被分配到邵阳师专(现邵阳学院)任教。从学生转变成老师,他心中对“师范”的理解更加深了一层,如果说高等师范院校的职责是培养立志于学术研究的年轻人,那么师范学校就是培养扎根基层、深入一线的小学教师,他们将带给懵懂无知的孩童们第一缕知识的阳光。在邵阳学院任教期间,石鸥工作认真扎实,主讲了教育学、心理学等相关课程。当时,他经常都是一个人在操场边踱步边思考,并给自己定下了条铁律——“整个一堂课下来不看一眼讲义”。正是执教初期的严格要求,他的教学水平越来越高,先后获评湖南省教学名师、国家级教学名师。石鸥说,“不看讲义无非就是两条,第一要对知识有了解,第二要对问题有研究。”他认为,大学老师一定要搞科研,并不是说正式发表到刊物上才叫科研,科研的含义就是真正对问题有研究。只有研究了,才能做到有见解、有看法,才能做到不看讲义,而如果没有深入研究,就只能照本宣科。在学术殿堂里,老师必须要有学术见解,对前沿领域问题,要有自己的看法。总是把科研和教学对立起来是不对的,科研与教学不是背离的,他们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大学的教学必须阐明问题,使学生树立“问题意识”,要做有深度的教学与科研。
文脉之承
“张之洞、严复、蔡元培、陈独秀……这些近代史上声名显赫的人都参与过教材的编写。不深入研究老课本,就不知道他们在这方面启迪民智的努力。”石鸥办公室的一面墙上,挂满了我国近代以来的教科书封面的复制品,这些是石鸥从他收藏的近2万余册教科书中精选出来的。封面的图画与文字,穿越了漫长时光,在今日仍然熠熠生辉。可以说,石鸥是它们真正的知音与伯乐。从兴趣使然的偶发到专业研究和收藏,石鸥在这条路上一走就是二十多年。他奔走于旧书市场,从布满灰尘的故纸堆里,淘出一本又一本消失在我们视野之外的老课本。对石鸥而言,抢救老课本是基于一种文化人的历史使命,他并不愿意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孤芳自赏,他委托专门的出版社翻印了“最新国文教科书”“最新修身教科书”系列,使老课本的文化之光撒播各处。石鸥悉心守护起这些来之不易的老课本,因为他们是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见证者”。
对于老课本的收藏和研究,石鸥饱含着充沛的热情,态度却又十分严谨和慎重,他曾对学生说:“研究老课本就像是考古,要像福尔摩斯探案一样不断找线索、找证据,用证据说话、让教科书自己说话。”石鸥对老课本视若珍宝却并非独自占有,他十分乐于同有需要的人分享这些“宝贝儿”,其中不乏一些故事。一次,一名陌生人致电石鸥,说他的奶奶年事已高,早已看淡人世,唯独对她父亲当年编的小学教材怀有一份难舍的情愿,只想再看一眼令她魂牵梦绕的小课本。为了完成老人的心愿,在老人生日前夕,石鸥将那本课本送到了老人手上,年近百岁的世纪老人竟至潸然泪下。看似平凡的薄薄一册课本,却跨越了岁月流转,串联起了世间的亲情夙愿。在学术研究上,石鸥更是秉持“学术乃天下公器”的原则,惠及四方,日本、新加坡、美国等海外专家也都多次拜访他,并因此成为挚友。小小的课本,消融了时间的界限,跨越了地域的限制,铺就了达到文化胜景的康庄大道。
石鸥不仅是老课本的一名研究者,更是一名优秀的老师。几十年的杏坛执教,桃李满天下,他的学生分处五湖四海,可都承续着石鸥的仁爱精勤精神。如今,石鸥的许多学生也已经晋升为教授,有了自己的研究生和研究团队,他们身上散发着的严谨治学的学术精神,这是从老师那里薪火相传秉承下来的。几乎所有的学生,都继承了老师的殷殷期望——研究着老课本,寻找着其中非凡的文化魅力,并让更多人关注到这个看似冷门却十分重要的课题。这同时也是一份鲜活的文化脉络传承,然而对于教科书的研究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后人不断求索。老课本收集的艰难,枯坐板凳的学术坚守,研究方法的创新与突破,仍是萦绕在石鸥心间的问题。坊间传闻中国老课本的价格飞涨,与石鸥对老课本的收藏保护有直接关系,石鸥也坦然承认如此说法。但这并非就是一件坏事,无论出于何种目的,老课本起码受到了关注,确实引起了收藏和保护的风潮,这对搜集、整理那些仍然散落在民间的珍贵教材有重要意义。以石鸥为代表的一批致力于传承老课本文化的专家学者,聚焦了社会和学界的目光,他们的不懈努力,汲汲以求,使老课本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随着时代的发展,它所凝集的书香和墨韵,让古老民族的智慧和荣光更加耀眼。
课本之思
对课本的热衷和咏思,不仅贯穿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求学时代,更折射出中国百年来的教育发展轨迹。教科书是时代教育发展的产物,是特定时期教育生态的高度总结和生动的反映。石鸥以数十年奋战在教育第一线的丰富经验,结合自身在教育领域多年来的深厚学术功底,全身心投入我国教科书的研究,他既深描百年中国教科书发展的历史,也深刻剖析“数字教科书”等未来教科书发展的趋势,他还竭力构建教科书的基础理论、探索教科书的评价标准等,全方位的把握隐含在教材中的中国教育的永恒思考,他所带领的团队正构筑起一个国内一流的、既有国际影响、又有本土特色的教科书研究大厦。
教科书到底该如何定义?也许不同的教育者和研究者都能罗列出一系列纷繁复杂的定义和学术化词汇。但石鸥对教材的定义其实很简单:“一种培养人才的重要工具,一个文明传承、文化创新的载体。”在石鸥看来,优秀文化的传承离不开一代一代的好课本去发扬。课本对人才的培养指向哪个方向,一个国家的未来就可能走向哪个方向。如果课本是传播真理的载体,那么其选录的内容就应该是人类文明的最精华所在,是我们在人类文明中、时代进步里最不可缺少的智慧。“课本是如此重要,所以我们要研究好它,要研究好它,我们就要有珍贵的文本做基础,有了好的研究才能矫正和批评现有的课本可能存在的问题。”石鸥所指的“批评”并非是对课本简单的研究分析得出的一份“标准答案”,他希望就像文学、电影、诗歌一样,对课本我们也可以建立起一套完备的研究和批评系统,而批评的目的在于更好的进步。“这个过程能带动大家都去做,每个人在学习的过程中课本也会越来越好。我们就是给我们孩子提供更好的精神食粮,因为课本在中国影响太深远,所以我们团队几十年都在做这件事,成果还是很丰硕的。”石鸥自豪地说着,而他手中的老课本此刻似乎也骄傲的焕发起光彩。
许多人对教材的理解无非是课堂死板的用具,比起传播思想、传承智慧的书籍而言,课本似乎更突出其应试教育的工具性,不少学生甚至见到厚厚的课本就“叫苦不迭”。石鸥认为教材这种文本与我们阅读的任何其他文本都存在不同,我们的阅读,或为消遣,或为研究,但是教材文本的阅读发生在中小学时代,好的课本会潜移默化对一个人整体的智慧框架产生影响,型塑其一生,一种智慧范式不仅是数理化、政史地的标准答案,更应该是一种能不断扩大、产生怀疑或者好奇的知识性体验,一种可以拓展的思维原型。“我们之所以成为现在的自己,是因为我们的读书和经历,而课本对一个人最初的思维方式影响是巨大的。”在石鸥看来,我们从老课本中能寻找到一种教育思维演进过程中真实的脉络,这种脉络中有被逐渐替代掉的残旧形式,同时也有值得今天继续研究和思考的传统智慧,在他的研究中许多旧课本中的经典得以重新出版重现,这不仅令如今的我们有幸得见那些珍贵课本的原貌风味,也得以对今天课本中淡化的趣味性和文化感寻觅到一份历久弥新的文化体验。
石鸥认为,对教科书的研究以及对课程改革的探索是殊途同归的努力,研究过去的课本历史并非是回顾曾经的文化沧海,而是为了完善滋养今日教育的繁茂桑田。今天教科书可以在国内外引起许多风波,甚至涉及到外交层面,这说明对教科书研究的价值不限于教育范畴,凸显了在国际化的大潮下文化生态的每一个部分都值得我们引起重视。概言之,教科书研究有它独有的价值和使命。关于课本的思考是一条漫漫征途,石鸥正沿着课本之思的道路勇往直前。“石鸥特色”的教科书研究立足过去、关心当下、放眼未来,在一定程度上开创了新世纪教科书研究的新纪元,他和他的研究团队将继续沿着这条道路矢志不渝的走下去。